本课题是中国资助型基金会研究的开篇之作,留待10年、20年之后,当资助型成为我国基金会主流模式的时候,其在公益革新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预期。 徐永光 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是以资助促进公益生态发展,这是付涛在《资助型基金会价值(案例)研究》之《综述》中开宗明义的表达,可谓切中肯綮。《综述》对于这项研究的背景、由来、研究方法、目标、研究过程及最终成果,作了条理清晰的阐述,值得认真研读。对中国第一批11个资助型基金会(包括转型中)的案例研究,颇具深度,对于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转型及公益生态系统的构建,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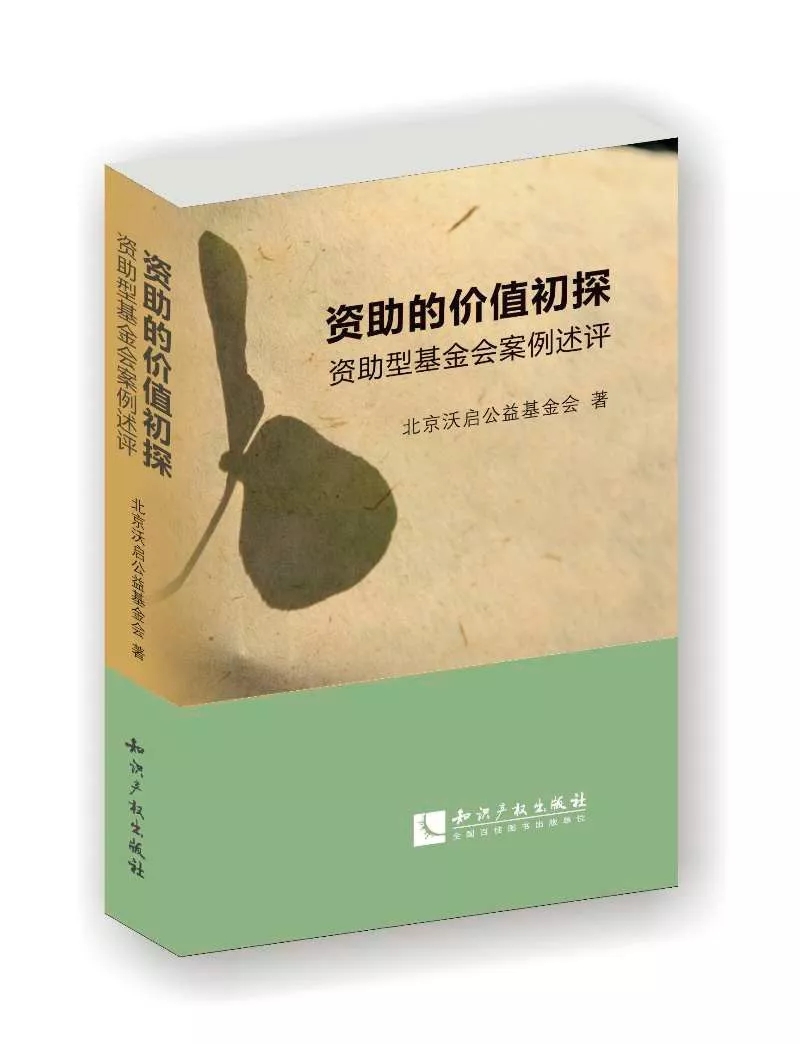
书名:《资助的价值初探》
作者: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本课题是中国资助型基金会研究的开篇之作,留待10年、20年之后,当资助型成为我国基金会主流模式的时候,其在公益革新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预期。
在中国65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的数量很少,可能总量约20~30家,不会超过40家”(引自《综述》)。从全球范围看,在公益价值链中,基金会基本上定位于资源供给者。类比商业,基金会一般做“投资”,不自己做“产品”。基金会与公益服务组织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美国为例,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来自个人的约占82%,来自企业的不到5%,来自基金会的占13%左右。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大部分基金会有自己的固定基金,在公益市场,基金会不是募捐者,而是资金提供者,是真正意义上“有钱出钱”的主;相反,中国的基金会是吸纳捐款的主体,且拿了捐款主要自己来花,做项目。中国运作型基金会占绝对多数,这个现状,并不反映运作型基金会与资助型基金会相比孰优孰劣,但可以反映中国基金会业态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中国特色所致。
分析原因,大体有三:
首先,不少基金会是由草根NGO转身而来的。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之前,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难以登记,不少机构只能登记为企业,很多公益人无奈“非法行善”。当时,我还在中国青基会任职,曾撰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指出“只有等非公募基金会出现,我们才有条件声明:中国有了真正的民间组织”,并给草根NGO朋友支招儿:借助《基金会管理条例》设定的法律许可,选择“造车上路”或“借车上路”。前者,筹资200万元,自己造一台非公募基金会的“车”,装上已有公益品牌的“货”,驾车上路;后者,游说愿意做慈善的富人或企业,让其接受你的公益理念和项目,出资成立基金会。前者的好处是独立性强,后者的优点是资金来源可靠。事实上,许多草根NGO就是这么做的,一批运作型基金会即NGO型基金会应运而生。有代表性的比如早期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后来的天使妈妈基金会、爱的分贝基金会。
其二,中国企业基金会数量不少,其特点是,既“早熟”,也不成熟。在美国,10万家基金会中,公司基金会仅有2700来家,慈善捐款来自企业的比重也很小。美国数量最多的是家族基金会、私人基金会,用的不是公司的钱,而是个人的钱,包括现金、股权、遗产捐赠等。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有一个小的公司基金会,用公司的利润来支持;而由盖茨夫妇办的家族基金会是个大基金会,由个人捐赠股权设立。
中国的慈善捐款,60%以上来自企业,这也是中国特有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富起来的是一批私人企业家,无论是出自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也好,为了提高企业的美誉度也好,抑或是担心“不共享就要被共产”(卢德之的理论),还有道德绑架因素,许多企业提前预支了自己的收益来做公益。企业办的基金会,多半会自己做公益,这也顺理成章,毕竟做资助型基金会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平,这并非企业基金会所长。
其三,草根NGO能力不足,与其资助他们花钱,不如自己花钱来得踏实。我与一些基金会领导人讨论时,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我则会谈四点不同看法:第一,草根组织弱是因为资源少,所以需要基金会多给资源;第二,找人做事比养人做事更有效率,如果资助一家草根组织项目做得不成功,可以换人,机构换员工可不那么容易;第三,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基金会责无旁贷,也需要勇于承担资助项目可能出现的失败风险;第四,公益是一个生态系统,行业整体好了,基金会也会活得更好,基金会要做热带雨林中的参天大树,不要成为沙漠中的胡杨树。还有一条,《基金会条例》把管理费用定得那么低,其中的立法思想就包含了这一点:基金会是公益资助机构,而不是公益项目的运行机构。
这些年,一批有实力的基金会,包括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开始向资助型机构转型,与草根NGO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共同成长,在推动公益行业价值链、生态链产生良性变化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
对于资助型基金会的未来发展,在五个层面存在突破的可能性:
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曾经在动员社会资源、弥补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创造了诸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优秀公益项目。这些“老牌”基金会影响力大了,发现在社会捐赠活动中,来自自然人的捐款笔数多,金额少,管理成本高;来自企业的捐款,笔数少,金额大,管理成本低,于是转而“理性”选择“大客户”战略。无独有偶,企业捐款人最喜欢项目的政府背景和捐款投入硬件建设。政府背景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而投资硬件由捐赠企业命名,是提升企业美誉度的最好软广告;对于基金会来说,与政府合作的项目,政府还可能匹配资金,参与管理,省了基金会很多管理成本。政府背景、企业青睐和基金会“傍大款”策略形成的“利益铁三角”,不断强化捐赠资金的硬件导向和向体制内的逆向流动,成为民间捐款回归民间的巨大障碍。而这种固有利益关系的惯性力量,成了这类基金会改革转型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
改革需要壮士断臂的勇气,而拿自己开刀何其之难。政社分离说了多年,也不见什么动静。办法只有一条—外部压力。要通过进一步建立基金会透明机制,让所有公募基金会公开捐款的流向,如果捐款流向政府账户,意味着这些基金会还在帮政府吸收民间慈善资源,应受到质疑。今非昔比,道理自明。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样有政府背景,一些历史较短的公募基金会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成立于2009年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在成立伊始就以“民间性、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为机构发展战略。其推出的“童缘”项目,资助了近200家儿童慈善组织,并由此形成儿童慈善领域的合作联盟。2012年儿慈会遭遇财务记账失误的“小数点风波”,受到媒体严重质疑,就因为机构的透明度高和草根NGO的力挺,不仅渡过难关,而且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和支持。去年的99公益日,中华儿慈会斩获捐款过2亿元,全年捐款近5亿元,近8成捐款来自个人。同为民政部直辖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也因为机构新,没有“老本”可吃,没有老路依赖,都选择了与草根NGO合作,分享公募权的道路,一样获得了合作共赢的骄人成绩。
这些机构的成功,可为那些老本丰厚的机构提供借鉴。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无论于公—支持行业发展,于私—机构的可持续性,都是有利的。
美国只有700多家社区基金会,但这类基金会在构建慈善生态方面的作用很大。不同于自己出钱的私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是公共筹款机构,类似中国的公募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纽约社区信托是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典型代表,其管理运营模式很值得中国同行借鉴。
中国社区基金会正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如果方向对路,可以成为整合社区公益资源、推动社会创新、改善社区公益生态的一种创新模式。社区基金会可以发挥五大功能。
功能之一,成为慈善信托的受托机构,为个人或企业管理慈善资产。《慈善法》为社区基金会慈善信托的设立提供了巨大机会。功能之二,成为小型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的慈善资产受托服务机构。功能之三,成为社区居民和属地公司员工志愿者捐赠动员的组织者。功能之四,成为草根NGO的资源供应者。功能之五,成为公益项目咨询和专业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各类社区组织。
要实现上述功能,关键在于社区基金会要有很高的专业化管理水准;而公益行业发展需要专业化支持,正是社区基金会大展宏图的时机。
中国数量巨大的慈善会,拥有大量捐赠客户和志愿者资源,最有条件按照社区基金会的上述5个功能进行改革转型,形成资助型基金会的强大体系。一些地方把慈善会变成了慈善联合会,作为慈善行业的自律组织,不应参与行业竞争,应把原来慈善会的募捐功能剥离,单独设立社区型慈善基金会。
中国富豪人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比尔·盖茨先生曾在他的基金会北京办公室对我说:“在中国劝说富人捐财产比美国来得容易,因为美国的富人大多是家族财富的继承人,不好做决定;而中国的富人几乎都是财富的第一代创造者,他们比较容易独自对财富的安排做出选择。”
中国正进入财富代际传承的密集期,已经出现一批捐款数十亿、上百亿的慈善家。从财富的积累到财富的传承,家族基金会无疑是富人财富的最佳归宿。与公司基金会相比,由家族私人财富投入设立的基金会没有商业利益诉求,因此更加纯粹,并能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美国的家族基金会数量很大,50%是规模小于5万美元的微型基金会。未来,中国的家族基金会也会以小型为主。小型家族基金会一般无力自己运作项目,会选择公益伙伴进行资助,成为资助型基金会的重要支柱。
2015年,美国富达金融集团所设富达慈善基金会的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advised-fund,DAF),账户余额达33亿美元,给慈善组织的捐赠额超过31亿美元,捐赠支出73万笔,超过了成立于1887年的美国慈善龙头老大“联合募捐”(UnitedWay)。富达公司有大量具有捐赠能力的客户,是基金会的客户基础;富达DAF与公益慈善行业密切合作,向客户提供公益慈善信息,满足了客户捐款投入的意愿。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富达DAF,账户数目从2000个左右增长到现在的8万多个,用于投资的基金会管理的净资产复合增长率超过20%。基金会的捐赠服务,也增加了金融公司所管理的资产规模,提高了客户黏性,为公司带来了新的收入。
这种金融+公益的模式已经引起国内众多金融机构和基金会的兴趣。尤其是金融机构借助客户资源的优势设立DAF,可以把捐赠资金、专项基金和慈善信托加以综合运用,把慈善资助和慈善资产保值增值都运作起来。DAF的突破和发展,将成为我国资助型基金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企业基金会多为成功企业所办,本身具备市场和创新基因,在中国公益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创新不足的今天,企业基金会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贡献给公益行业,为建设和改善公益生态做出贡献。公司基金会选择业务熟悉的领域,借助企业自身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成为该领域公益伙伴的支持力量,可以做到得心应手;如果加上用心学习,认真规划,还可以游刃有余,成为该公益领域的引领力量。
以上仅就我国资助型基金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条件、文化环境和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未来变化的可能性,谈点粗浅看法。对于本书内容,除了高度首肯之外,不敢多作评论。无病呻吟,蛇足之议,非我所愿矣!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