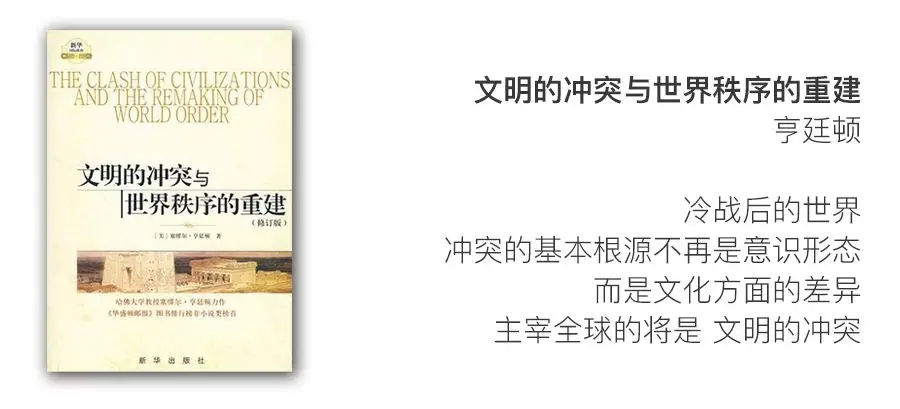2012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正式提出,经过数年,如今每座城市以及众多乡镇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12个词语,每一个都有丰富的内涵甚至不同的细分。
这是一套美好的表述,南都观察曾在2016年以此为基础,整理过一个书单,并且在历次互动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图书作为礼物赠出。
过去的书单随着过去的账号消失了,如今我们更新了这份书单,每期学习两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更新完毕之后,将有一个全新的互动正式推出。这是第二期。
▍文明:彬彬有礼,仁德有序
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在《尚书·舜典》中写道:“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曰:“经天纬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批判20世纪上半叶法国混乱的历史教学,他希望展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流畅易懂、自然而然的叙述,学习历史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混乱,而不是连历史人物的年代都辨别不清。为了呈现出这种简洁、流畅,布罗代尔索性自己写了一部《文明史》。他还在书中写道:“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则因一部《人类简史》一举成名,总结了人类从石器时代至21世纪的各种演变、变革,在书中,他还将人类的新科技和原本看似毫无关联的古代文明相对比,比如将在鼠背上培育耳朵的实验与三万余年前的施泰德狮人雕像联系在一起,产生奇特的关联和想象。他还忧虑未来科技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当人类寻求永生,而最终可能只有极少数人能负担得起永生的代价,文明会走向何处?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则关注历史上一个个闪光点,它们是西塞罗在古罗马帝国的人生起伏和珍贵而巨大的文化遗产,是“庸人”鲁热在一夜之间创作出《马赛曲》的“高光时刻”,是探险家巴尔博亚的那双历经艰险之后终于望见太平洋蓝色海面的欧洲人的眼睛,也是英国人斯科特在争夺“第一次到达南极点”的风暴中的坚韧和绝望……
利昂·P·巴拉达特则关注“意识形态”这一人类文明中的新事物,他曾经历冷战,也看到共产主义世界的衰退、恐怖主义的兴起……还有环境主义、女性主义、军国主义等等分类,它们源自何种价值观?将会构成怎样的政治体系?当经济、文化、科技已经在全球不断流动,人类已经越过了国家的边界,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是偏见应该如何相处?这些从人类文明中演变出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是文明对我们的新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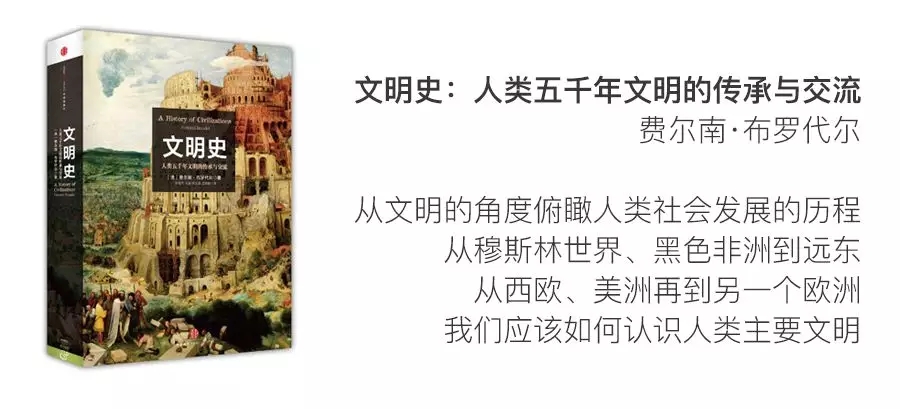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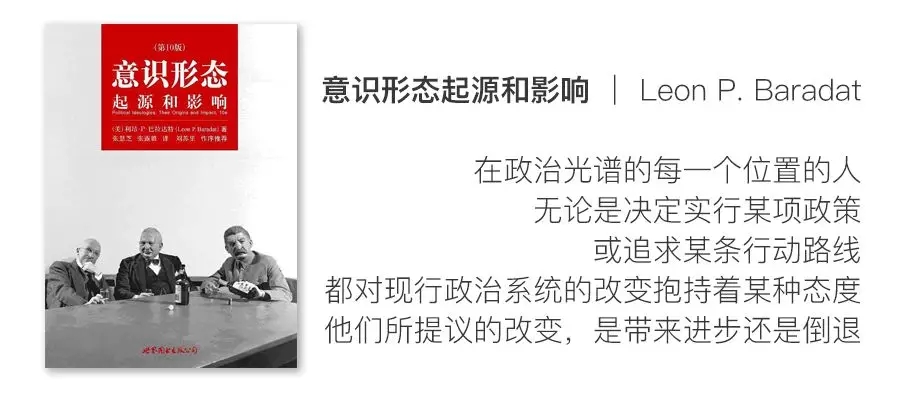
▍和谐:多元包容,以和为贵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构造和谐社会所包含的和平、和气、和睦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生命哲学。在《论语·子路》表达,“君子和而不同。”《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亨廷顿因为预言“文明的冲突”而成名,他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此时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不同文明间融合的可能性较小。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在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这一层面上,费孝通提出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他对于“文化自觉”理念所作的概括。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复杂的结构,这复杂的结构是起于它悠久的历史。经数千年文化特质自身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传播,才形成现有的状态。它复杂的结构就表现于各地文化的变异中。在《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的序言中提及:“文化自觉的确是时代的要求,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世界各个民族也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这样才能形成世界各种文化多元共存、取长补短、联手发展的局面。”
在英语中,宽容一词来源于拉丁文tolerare,即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或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在《宽容》一书中,房龙描绘了在西方文化最显着的脉络——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中,人类是怎样不断与“不宽容”做着斗争。宽容意味着个性与自由,而发现个性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进步。他在书中说:“生命本来是一次光荣的冒险,结果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生存完全被恐惧所笼罩。”
茨威格也看见过这种强加的“恐惧”,但他依然说:“真理可以传播,但不可强加。”历史上有太多针对“异端”的猜忌、伤害、屠杀,而所谓“异端”,不过是族群、信仰、思想等由不同地域、历史、文化演变而来的人为判断,它们都无法超越“人”本身,为此,茨威格还说:“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只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的信仰,只应为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